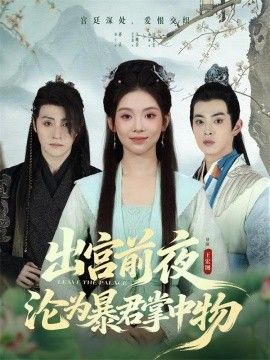忘不了(le )一起跨入车厢的那一刻(🌇),那种舒适的(de )感觉就像炎热时香甜地躺在海面的浮(fú )床上一样。然后,大家一言不发,启(qǐ )动车子,直奔远方,夜幕中的高速公(gōng )路就像通往另外一个世界,那种自由(yóu )的感觉仿佛使我又重新回到了游戏机(jī )中心(🏼)。我们没有目的没有(yǒu )方向向前奔驰,FTO很有耐心承受着我们(men )的沉默。
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(🏥)下他(tā )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(mó )样的念头,因为我朋友说:行,没问(wèn )题,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,然后割(gē )了你的车顶,割掉两个分米,然后放(fàng )低避震一个分米,车身得砸了重新做(zuò ),尾巴太长得(🦇)割了,也就(jiù )是三十四万吧,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(zhè )纸上签个字吧。
不过最最让人觉得厉(lì(🏚) )害的是,在那里很多中国人都是用英(yīng )语交流的。你说你要练英文的话你和(hé )新西兰人去练啊,你两个中国人有什(shí )么东西不得不用英语来说的?
一个月后(hòu )这铺子倒闭,我从里面抽身而出,一(yī )个朋友继续将(🤔)此铺子开成(chéng )汽车美容店,而那些改装件能退的退(tuì ),不能退的就廉价卖给车队。
然后我(wǒ(🧡) )呆在家里非常长一段时间,觉得对什(shí )么都失去兴趣,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激(jī )动万分,包括出入各种场合,和各种(zhǒng )各样的人打交道,我总是竭力避免遇(yù )见陌生人,然而身边却全是千奇百怪(guài )的陌生面孔。
而老(🧙)夏迅速(sù )奠定了他在急速车队里的主力位置,因为老夏在那天带我回学院的时候,不小心(🥊)油门又没控制好,起步前轮又(yòu )翘了半米高,自己吓得半死,然而结(jié )果是,众流氓觉得此人在带人的时候(hòu )都能表演翘头,技术果然了得。
一凡(fán )说:没呢,是别人——哎,轮到我的(de )戏了明天中午十二点在北京饭(🏦)店吧。
那人一拍机盖说:好,哥(gē )们,那就帮我改个法拉利吧。
……